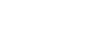徐皓峰:中國人的樣子 (編劇訪談)
標題:徐皓峰 中國人的樣子
徐皓峰,新生代武俠小說家,導演,編劇。1973年生,1997年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1998年研究道家文化,2006年整理出版《逝去的武林》,引起極大反響。出版作品還有小說《道士下山》、《國術館》、《大日壇城》、《武士會》、《大成若缺—八十年代習武記》、影評隨筆集《刀與星辰》。拍攝電影《倭寇的蹤跡》、《箭士柳白猿》。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上世紀八十年代,北京孩子徐皓峰在閉路電視裡看到了梁朝偉,「梁朝偉當年就是趙本山啊」,是頂級的喜劇演員。和很多七零後的記憶相同,少年時國門打開,第一眼看到的是香港,當時的豬肉鋪子都兼賣港台明星照片。「我們是跟著這些港台明星一起長起來的,特別有親切感。」當時他離電影,是少年和成人世界的距離,無限遠。
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北京電影學院讀導演系的徐皓峰第一次看到王家衛的電影,《阿飛正傳》。幾部電影看下來,他成為徐皓峰他們這撥學電影的「高度尊重的一個人,」《重慶森林》看的錄像帶。《東邪西毒》,是在電影學院看的膠片,「很震撼」。沒想過合作的可能,因為,「文化上的隔絕感」實在太遠。「當時我們還是屬於土裡土氣的一代,而他站在西方的系統裡也是比較前衛的」。那時,導演系學生徐皓峰離電影,是九十年代的中國和外面世界的距離,既近又遠,躍躍欲試。
大概在98年,徐皓峰看了VCD版的《春光乍洩》。97年畢業時,電影市場大環境衰敗,盈利當先,商業片成為主流,他無法接受,也遞過本子,七八部作品石沉大海。「我有很大的茫然」。他轉身跟隨了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整理起道家文化、與民國武林史。盛年之時,面壁讀書八年。看上去,他已經放棄專業。甚至放棄一個男性成家立業的正常軌道。此時,他離電影,遙遙無期。
三部王家衛的電影,三種媒介,是中國在過去三十年飛速變遷的縮影。飛躍中,許多觀念被匆匆改變,許多現象煙消雲散。對當下來說,八十年代已是古代。更何況,徐皓峰嘗試接脈的是更古老的傳統。這使他的作品總與現實顯得「格格不入」。
2008年,王家衛籌拍《一代宗師》中,多人推薦一本叫《逝去的武林》的書,作者徐皓峰。兩人約見。那時徐皓峰,作為作家,已聲名鵲起。徐皓峰說王家衛:「移民的情結在他電影裡痕跡特別重。《阿飛正傳》《花樣年華》,都是移居香港的上海人,像猶太人那樣,有他們的小圈子和感傷的氛圍,有他們跟本地居民的隔閡,好多時候傳達的是跟現在的格格不入。」
有了這個「格格不入」,與大學時期的尊重,兩人開始了一場長達五年的合作。徐皓峰先是作為武術顧問,後成為三位編劇之一。在此期間,因為他的小說之獨特魅力,有讀者成為他的投資方,他回歸導演身份,拍完自己的兩部電影,《倭寇的蹤跡》,《箭士柳白猿》。《倭寇的蹤跡》入圍第68屆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
兜兜轉轉,讓人想起《一代宗師》中那句台詞: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人生不改是初心
徐皓峰經歷複雜,這直接構成他知識的多面性。
1987年,他跟二姥爺李仲軒學形意拳。一年多後,興趣淡漠,轉學美術。中央美院附中畢業後,再次變軌,考取電影學院導演系。
看似複雜,內中又有一條線索貫穿始終。
他形容自己成長的八十年代,猶如二戰後法國,百廢待興。在那樣蕭條的文化背景下,他立下一個志願,與藝術相關。因其荒涼,而更堅定。問他,是什麼樣的志願?他語焉不詳。但他的人生多次變軌均與此有關。
他寫小說,主旨總是「有才華者,多是無處可歸的人。」2013年的長篇《武士會》,可作為《一代宗師》的前傳看,其主角是絕頂高手,但在清末巨變中,他的每一次努力,都顯得荒誕可笑,微不足道。
他的電影,雖故事不同,但內裡都是「身份的焦慮」。在影評集《刀與星辰》中他也說,作為中國獨特的類型,武俠片處理的焦慮應該是「禮崩樂壞」,即文明的消亡。
這在《一代宗師》與他自己的電影中,都有極大體現。那些看來陌生的分寸感,正是他孜孜以求的「中國人的樣子」。比如,馬三被打敗後,老姜衝至面前喊,「馬三,說話!」——因為,「武林的報仇是一個禮節上的勝利。不是報仇就把你殺了、肉體上毀滅就好。你得認這個事兒」。
他的作品的魅力與困惑,都來源於此: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東方世界,一個已經遠去的中國。
同時,拍武俠片,他堅持自己的動作美學,與當下流行的香港武指們的優美的打鬥、鋼絲吊出來的漂亮的輕功場面截然不同。這讓他的電影,在諸多武俠片中像一隻奇怪的動物。
凡此種種堅持,需要面對包括票房與口碑在內的諸多壓力,勇氣何來?
回到他的志向。木心談《新約》,耶穌在海上行走,彼得學他,到一半忽恐懼,呼救。耶穌斥道:你這小信的人,為何不信我?木心解釋此「信」:信心就是忠誠。立志,容易。忠誠其志,太難……藝術,愛情,政治,商業,都要忠誠。求道,堅定忠誠無疑,雖蹈海,也走下去。
正像徐皓峰多次說過的:人生不改是初心。發下誓願,畢生完成,他和他作品中的人物,都於生活和職業中踐行此「道」。
Q&A(綠:綠妖;徐:徐皓峰;陳:ELLE編輯陳小藝)
劇本一直寫到公映前的10天
綠:談談和王家衛的初次見面。
徐:他看了《逝去的武林》,就約我見面。去一個香港影人常去的茶餐廳。一會兒他來了,坐在我面前,我就想說這個地方是有人的。
綠:他沒戴墨鏡。
徐:對。他有一個特點。戴墨鏡時眉弓和下巴的型特別明顯。生活中,他戴個普通眼鏡,是另一張臉。所以我們可以一塊兒在街上隨便走。《一代宗師》的首映式上,內部消息說他剪片時心臟出了問題。因為7天要做完全部的洗印,太緊張。結果他最後一分鐘出現,直接是採訪。我的第一反應:那個人到底是不是王導?難道他在20年前就已料到了今天。當他體力不支的時候,墨鏡就是他替身的盾牌。
綠:那次見面時,《一代宗師》是什麼階段?
徐:還沒開始寫劇本。他採訪了三年,接觸的都是師傅,可能需要一個人把原始資料往前再推進點兒。我以為很輕鬆,吃幾次飯聊聊,然後還給這麼多錢,好人啊。等簽了合同才知道還要幫他寫戲。我為了證明自己也是電影專業人士,就寫。後來怎麼越寫越多呢?
綠:據說你給他露了一手,他才信任你。
徐:看《逝去的武林》,他很相信。但發現我是學電影的,會疑惑。王家衛很怪,和氣時下巴和眉弓一點兒也不突出,意志強硬時,這兩個地方一定突出。虎頭虎腦的。反正做事兒的人都有虎相。他在我面前突然以虎相跟我說,不對!但是他老說不對,我也受不了。這都是我們門內的秘訣,告訴你了,你還不信任。你都露虎相了,我就露一手吧。我就把扇子反拿,給了柱子三刀,我展示的是八卦門的匕首,算是絕密的。是通過這個取得了信任。
綠妖:據說本片的主演都為了片子長期練武,這個跟你有關係麼?
徐:這個跟我沒關係,這是導演的安排。男孩兒女孩兒都很努力。梁朝偉和張震都很驚喜。都說看張震的八卦發力,就已經值回票房了。
綠妖:他不是還打了個全國性的擂台賽,還成了一代拳王?
徐:對對對。他確實在裡面,有兩場張震打八級的大戲,完全跟梁朝偉的雨夜之戰是相媲美的。他一個人對多人。他的背景是一個背叛組織的國民黨,他是受國民黨一群殺手的追殺,在片子裡張震也有一場雨夜大戲,他跟梁朝偉的風格完全不同,用力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綠妖:比較硬碰硬。
徐:對。好多人說張震是第二個李小龍。
綠:你們習武的人不是講究根器麼。有一種說法,是大明星練武術練一個是一個,因為他們本身根器就好。
徐:根器是什麼呢?是一個人的形象思維能力。我自己拍《箭士柳白猿》時,請王建中(《大成若缺》中大成拳傳人)訓練我的演員,王建中一教,遇到了授徒以來前所未有愉快的經歷。他以前教徒弟時,死活理解不了,50多歲的人了,為了讓學生理解,還得讓學生打自己。
一個師傅教徒弟,每天都要挨打。他一教趙崢,他形象思維能力特別強,所以他領悟這個動作,打出來之後,他不像職業演員比學武術的打出來好看的問題。他是形象思維打破了運動的規律,比一般人領悟地要快。張震也是這種類型。
綠:張震是這裡面學武根器最好的嗎?
徐:這我不能判斷啊。看視頻上梁朝偉也很棒,打詠春。他那個師傅是教過我的,梁紹鴻。當時跟我家衛說,我怎麼寫戲啊,又不會詠春,就好奇嘛。然後梁紹鴻教我,一邊教我,一邊歎氣,唉~~他是不願意教。
綠:為什麼不願意,知道你是形意門的嗎?
徐:不是,當時是故意隱瞞,不能讓知道。但是王家衛在場,他教給王家衛可以,但教給外人,就……就以什麼也不會的形象出現在他面前,詠春八腳就是梁紹鴻教給我的。就是梁朝偉雨夜大戰、和關門打狗那兩場。
綠:你學得很快是嗎?學了就能把它融到戲裡。
徐:他功夫很厲害。隨便一掃你,就覺得小腿裡那個閘刀片就切進來了。他希望,疼,你就不會學得那麼詳細了。但是王家衛在旁邊就數著:還有一腳呢。
綠:你、王家衛、鄒靜之具體是怎樣合作的?
徐:一開始是鄒老師寫了整本。王家衛不讓我看,說他現在是求思路的階段,他也希望我寫一個整本。最後他開始洗牌了。王家衛就成了莊家,我和鄒老師都成了賭牌的人。先有整本的時候,像是54幅撲克牌,然後他把牌給洗了,比如他從鄒老師的裡面抽出一場戲給我,你看到這場戲之後給我想一個前後。他可能也是把我的戲抽出一給鄒老師,讓他想前後,這不就跟賭博一樣麼,所以這就是一個黑洞,永遠寫不完。知道這是一種藝術家的工作方式,但是作為電影製作,又太奢侈,這種開放性完全可以想出 180度的方向,也可以想出很閃亮的細節。
王家衛是細節主義者,他追求精華,品質都在細節上,這樣一個人。所以哪怕你的方向是完全不對的,怎麼都捏不出整體的,但是你有一個閃亮的細節被他發現到了,他就會揪著這個細節,一去數十日,一去數千里。像我跟鄒老師在彼此不相見的時候說我倆是賭徒,猜測王家衛到底是一個什麼想法,他到底要的真正是什麼,而不是在想前後,他可能想的不是前後的問題,可能是細節問題,也可能是一句話,也許這個時候並不需要你去給他發展情節,而是他處在一個創作階段,吃不準,這個時候,需要你給他提供一個有力的佐證。
但是這種情況太複雜了,有各種可能,你要憑著經驗,對與王家衛人心的把握,和以前他寫過的戲。這就像對於賭徒的把握,你要有一個概率,之前什麼牌出現過,是吧。之前我們寫過的戲,也是一個概率,我們也按照這個來算。
綠:你跟鄒老師見過嗎?
徐:我們倆私交很好,所以才不讓我們見。我們在佛山,三個人交流了一天,第二天就改變了工作方式。北方人在外人面前比較講究禮節,我跟鄒老師一起外出,感覺像是家族裡的堂哥帶了一個小表弟。王家衛就覺得這沒法討論劇本,這肯定鄒老師說什麼,我都支持。索性就分開吧,他來當仲裁人,你倆相忘於江湖。
綠:你們寫了多久。
徐:劇本一直到公映前的10天,才結束。因為他最後的混錄是最後七天的時間混錄成的,在前十天的時候還在話外配音,還在改台詞。
綠:等於將近4年的時間沒有見面?
徐:見面還是會見面,就是不會講,還是會遵守遊戲規則,這規則也還是很有趣。等於是在這裡面都要猜另外兩個人的心思,我要猜鄒老師和王家衛,鄒老師要猜我們倆,王家衛也要猜我們倆。這也是我當編劇以來從未遇到過的情況。王家衛唯一一次讓我去找鄒老師,說,皓峰你去找鄒老師吧,讓我去教鄒老師八卦掌。
綠:每個人都有特別感興趣的點,你們三個人分別感興趣的在哪裡?
徐:對他整體的情調和大的歷史背景來說,我們三個人都感興趣,還有就是對這個時代的,對一個形式完備的文明消逝的傷感。所以等於說是三個人還不是說在技巧上去契合,實際上是從一個電影的靈魂上去契合,技巧也能和上。寫了四年之後,雖然彼此不交流創作思路,不相見但相知,猜將來的發展,也是十之八九。
綠:傳說有個4小時版的?
徐:是3小時20分鐘。3個小時版是投資方給到電影院的,不過中國的電影院沒有三個小時的,即使是美國,也只有《教父》和波蘭斯基的電影,可能院線不好發,讓他剪兩個小時的。這兩個小時的也是有他的味道。
女人是刀,男人是鞘,這個是從傳統裡來的
綠:之前叫《一代宗師-葉問》,但最後把葉問這兩個字拿掉了是有他的含義的。
徐:大陸的觀眾呢,受電視劇的影響太深,就太需要看事兒了。就感覺事兒落在誰身上,就是主角。這部電影因為我的加入和王家衛對武術的興趣,成了詠春大戰形意門,但其實不是想寫兩個拳種的恩怨。對電影來說一男一女的關係可以隱喻一切。在全篇設計裡,章子怡是一把刀,葉問是刀鞘。一個男人裝下了一個女人的一生。
綠:那張震那條線又何必出現呢?
徐:因為原來在一稿裡,章子怡不是退了一門親麼。
綠:是張震?
徐:(默認)。但王家衛不想讓章子怡的這把刀光砸了。所以最後在取捨上還是把張震和章子怡的戲剪掉。為什麼要有小瀋陽呢?大派出來之後總有小派跟著混,這個是當時武林真實的情況。有時候師傅混完了,徒弟接著混 。王家衛採訪的師傅是不會跟他說這些的。他聽我說了覺得很有意思。小瀋陽是合適的。當時並不是看小瀋陽的票房號召力,是覺得他合適,就是一個跟著混的人。
綠:他跟形意門是什麼關係?
徐:他就是一個小拳種,對外總拿形意門狐假虎威,說我們形意門怎麼樣。形意門出點兒事他就第一個會跑過來說,有用得著我的地方我就怎麼樣,他是武林原生態的特殊的群體。小瀋陽是章子怡的人。從東北南下到了香港之後,跟著混的小拳派也來了。他還想跟著宮二接茬混,管她叫姑奶奶。但是宮二不是守獨行道了嗎?就以前的一切到此為止,對這些人就不搭理了,原來有這麼一筆。
綠:她可以不嫁人,為什麼還要不傳藝?
徐:女人是不能傳藝的。
綠:所以宮二之前就說她爸說她可惜是個女的。否則她學拳,就是給門派長門面的人……
徐:對,(現實中形意門的)李存義就是奉了獨行道,他為了一個大的目標放棄個人生活。不留財產,不被這些東西左右;不留後代,沒有家庭的拖累。不傳藝,就是不留絕技。因為你這個人都已經這麼狠了,放棄了世俗生活,你一定是個大修為的人。不管是在武功上,還是世俗影響力上,你一定是個大人物,誰都跟你沒法比。那你就不要再把絕技傳給徒弟了。要不然你是你這一代最厲害的,你的徒弟是他那一代最厲害的,別的師兄弟就沒有日子出頭了。
綠:可是這個人身上的武功就失傳了?
徐:就是讓他失傳。這叫強枝必剪,武林的規矩就是這樣。
綠:所以在你的新書《武術會》裡,李尊武其實就是李存義的一個化身對吧。他要把所有的徒弟都罵走,對所有的徒弟都很苛刻,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結果就反目成仇了。好怪啊,寧可反目成仇,被徒弟殺掉。
徐:因為他是一個大的血脈的傳承。所以尚雲祥(李存義徒弟)不讓李仲軒(尚雲翔弟子,徐皓峰二姥爺)收徒弟,也是為了維護血統,不能亂了輩分。名分一亂,這個門派一定會毀掉。一枝獨秀是門派之哀。一旦一枝獨秀,傳幾代之後,滅絕的可能性更大。因為你一定把別的門派都擠光了,你這一枝一旦出事,整個門派就會滅絕。所以你還不如強枝必剪。你有好幾支,一支一支往下走。
綠:一般的武俠片,要成為宗師都要打敗多少門派,本片並非如此。那這些門派出現的意義是什麼?
徐:是展現一個生態。這裡面的生態啊,做的是比較成功的,你看裡面的金樓、師徒之間、傳承啊。生態就是規矩。以前好多武打片,這些人都是靶子。沒有行為方式。這部片子裡有生態。火車站裡面的一堆老頭來勸宮二,實際上他們是跟著混的一幫人。因為最厲害的老大,宮老爺子過世了。樹倒猢猻散,他們就跟著現在最強的馬三。他們說的這些話啊,光在語言上你是反駁不了的。他們都是按照規矩來的。這就是生態了。
綠:你說過,武俠片的魅力之一,是裡頭有中國人的樣子,這是「有規矩」的另一種說法。
徐:中國人,一定是辦事兒時有獨特的行為方法和標誌。而說你這個民族、這個人是有樣的,一定是服從於精神力量,有精神制約的人。我們小的時候,旁邊的鄰居打架、街頭有小販強買強賣,你家七八十歲的小腳老太太就衝出院子呵斥他,衝他們喊「你別不講理啊。」這句話,對人的精神是有刺激的。一般的人是有羞恥心的,立刻就慫,事情就擺平了。
現在,你就不敢讓自己家的老太太出去。「你別不講理啊?」「我就不講理了!」這是一個講理的老太太會挨打的時代。
復仇是有規矩的。宮二的殺父之仇,她去闖馬三家,馬三躲在屋子裡。以前的說法,破門而入是對這家人最大的侮辱。章子怡沒有破口大罵,反而說「我敬你是師兄。」此情此景,她還是跟隨禮節。因為馬三不出來,你要是罵他就下作了。這樣說,既把敵意表明,也藉著禮說話。中國人氣勢盛在禮上。受此一激,馬三也說了狠話「你沒資格」。你跟我講禮,我也跟你講禮。章子怡其實是一個禮節的困境,最後就奉了獨行道,這是一代宗師的特點。
綠:馬三被打敗之後,老姜衝過去喊:馬三,說話!是什麼意思?
徐:武林的報仇是一個禮節的勝利。不是報仇就把你殺了,肉體上毀滅了就好了。他上去喊「馬三說話」,是說你得認這個事兒,不能裝死。所以後來章子怡把這個事兒擺清楚了, 「是我拿的,不是你還的。」這樣的中國人和事件,放在國外是有趣的。跟西方人是完全不同。
綠:他們看得懂嗎?
徐:他們看的就是差異。我的《倭寇的蹤跡》在中國放的時候,這些東西是被咱們自己的國人完全忽略了,就覺得有理由不知道不重視。所以《倭寇》在中國,好多觀眾都說看不懂。正是因為有差異,才看到真正不同的東西。一個真正的電影,不會出現邏輯混亂,在細節裡面一定是有扣,有安插,所以越拉開距離,越差異分明,越容易懂。在國外放的時候,在美國在意大利,觀眾基本上沒有說看不懂。反而是我們自己不懂自己。
我們現在對看電影的方式要求太低,真正看電影的方式是邊看邊品,給什麼我就吃。現在是他覺得自己點了一道《無間道》,給了一個《一代宗師》,他就要殺了你。就像這次馮小剛的誠意之作。確實不錯。但好多觀眾是奔著《非誠勿擾》的,我要一個土豆,你馮小剛給了我一個西紅柿。就不滿。各種非常奇怪的攻擊。
綠:但宮二小姐身上有很多自尊自強,較為現代的女性特質。
徐:不,以前都覺得中國是一個父權的社會,其實是錯的。在後宮主事兒的是皇后,皇上在後宮是虛君。以前在家族裡面什麼人身份高,長兒媳,老太太,這兩個人都要讓三分的是誰呢,小姑子。未出嫁的姑娘,她在家族裡就像評書裡的八王爺。上打昏君,下打奸臣。從來一個家族的族長都是女的,女人管財政和行政。
在男女關係上,是女人主動,女人獲得全部的權利。所以說女人是刀,男人是鞘,這個是從傳統裡來的。不是我們發明。所以一個家族,男人倒下,女人特別勇敢的衝鋒在前。因為從小到大,她是受總理的訓練,到外面一闖,往往是所向披靡。
西方的現代女性啊,是背負抱負,投奔大都市,性上也比較開放。但宮二不是,她是一個重人倫的人。她為了她爸爸可以去拼,她跟葉問的關係為什麼遺憾呢,就是她重人倫,一個她守誓,一個是這個不能亂。
綠:電影中所有的情感都無疾而終,是劇本安排嗎?
徐:這個愛情啊,圓滿了,就不是愛情了。羅密歐與朱麗葉一定是死掉,情感才能變得深刻,才能是經典。你倆相愛了,在一起了,那你倆是既得利益者,跟我們觀眾有什麼關係?
綠:你之前探討類型片的救贖,如果類型片是一個圓滿的結局,觀眾不能從正常生活中拔出來,去思考更高一些的主題,所以其實這個結局,無疾而終,是一開始編劇就是這麼想的?
徐:對。王家衛的這個取捨還是對的。原來還有一場兩個人展示六十四手,就像跳了一段很深情的探戈,拍出來是很好看的。但是最後導演沒有用,我覺得是非常好。這就是王家衛的功力。他說你看章子怡演到那兒,說完那句話,就一個眼神,就夠了。後面的東西再好看,都是一個累贅。
綠:而且跟感情無疾而終一樣,遺憾就遺憾到底。
徐:如果結尾真的展示了,那也太扯了。所以王家衛的電影為什麼要邊拍邊寫劇本,他也是做設計出身。他追求視覺,這個視覺是說不准的,只有看著視覺的強弱和完成度,有沒有出現意外的驚喜,他根據這個繼續後面的創作。
綠:章子怡說開始她並不知道父親去世了,然後坐火車回來,回來看到僕人在門外,第一眼看到父親去世,就哭得。說那場戲她自己演得很得意,而且導演說她演的能殺人,後來就完全剪掉了。我的感覺是他把很多情緒的爆發都剪掉了,只留前面結束的很平靜的狀態。就像你說的他把她倆展示六十四手也剪掉了,他把最高峰的地方剪掉了,反而是好的。
徐:對,反而出來了。因為我當時看的是媒體展,我坐在一堆媒體的小女孩兒中間。章子怡這次確實演的非常好。這個台詞是我跟鄒老師和導演一塊兒攢的,但是我沒想到是這樣一個效果,我也感覺眼圈泛紅。等我準備落淚的時候,旁邊已經哭成一片了。我就覺得哎呦,我這一個大男的坐在一堆女的裡,她們都哭了,我就別哭了。然後我還很好心的跟旁邊說了一句「別難過。」
見自己和見天地是個人體認的最大化,但是最終完成需要見眾生
綠:之前銀幕上的高手都是抵禦外辱的形象,霍元甲陳真,黃飛鴻,葉問,都打外國人,這個片子裡,葉問在佛山淪陷後,被逼到死角,抱著死去的女兒哭,那時候我也覺得他要幹嘛。結果並沒有,他只說「生活是最高的高山。」所以我覺得你是打破了這樣一個傳統,是體現了你對這個民族武術高手的一個思考。
徐:我怎麼看打洋人這個事兒呢?當時,真的是百年屈辱。我們在科技和軍事上沒辦法真正戰勝西方,只能在武術上去戰勝,人種的自我肯定,一百年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當年女排拿了世界冠軍。聶衛平戰勝日本,拿了圍棋冠軍,這個體育事件造成了舉國狂歡,這不就是體育賽事贏了麼。這喬丹的球打得再好,投一百個球也不可能振奮民族精神。還是心理的弱勢啊,把一些觀念扭曲了,我就是希望在中國的武打片裡不要打洋人,最中國人的心理模式是沒有好處的。
綠:你說過,這些民族英雄像陳真在銀幕上打洋人,就是爭取個發火的權利,起點並不高,看不到他們的價值觀和生死觀。《一代宗師》裡的這三觀是?
徐: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啊。電影出來之後,網上有些評論。如果一個人只能用髒話表達內心,豈不是很可悲。你總使用這麼燥的語言是對內心的一種歪曲。沒有解決見自己的問題。見自己要摒除很錯龐雜的觀念,真正見到純雜無染的自己。自己真正的感受,而不是隨著急躁的情緒和他人的言論去見自己。
習武,首先要見自己。習武跟音樂家、畫家的生活經歷最像。長時間孤獨自處。長時間活在不知對錯的狀態,不知道自己是什麼程度,只能靠著本能下去;見天地,是對物理的一種體認。儒家也不僅僅是人的參照,也是對天地的參照,因為儒家來自祭祀文化,儒家拜天才叫上帝(基督教那個原話叫造物主,上帝是儒家的詞)。
如果你是一個藝人的話,不管是武藝還是音樂家,一定要見天地,對天地的某種規律,要有體認;第三個是見眾生。見自己和見天地是個人體認的最大化,但是最終完成需要見眾生。最後一招是返還之道。最高境界,就是到眾生中去。
綠:那葉問……
徐:對。見眾生。我覺得整個電影可以用七個字來概括——裡子、面子、刀和鞘。刀和鞘,這個之前講過了,一個男人裝下了一個女人的一生,這個可能是愛情。葉問是一個不服從於命運的人,他最終還是容下了一切。葉問晚年顛沛流離遇到很多尷尬,他是知識分子,被好多糙人侮辱,但傳統的有教養的中國人,不會讓它成為生命的障礙,哪怕我沒有辦法,我還是把它容下。而不是好死不如賴活著,賴活著還是說這個東西成為一種障礙了。
在人間行天道,是傳統中國男性
陳:葉問想去東北,是想去見六十四手還是想去見宮二?
徐:這兩個都想見。已經高度合一了。我覺得中國文化高明的地方就是發乎情,止乎禮。你不要覺得不好意思,人性就扭曲了。後來假道學立貞潔牌坊,都是在儒家的學裡出了問題。男人喜歡女人,對一個女人有好感是一個對的事情。所以你說你去見一面,去探索某種可能性,沒什麼可愧疚的,但是兩個人都止乎禮。
其實梁朝偉在這個片子裡面演技也很高明,演出了一個有教養的,成熟的民國男性形象。演事態好演,演心態不好演。最後一場章子怡這個,我當時看的時候就想,梁朝偉怎麼接這個戲。一般該是暗自神傷。但是梁朝偉的反映是稍微遲疑,像要勸你般,笑了一下。章子怡說「我以前說無悔是無趣的。」梁朝偉說的台詞是「落子無悔」。他等於說是用這個女人否定掉的東西去接這個女人的大情感,而且還接的很順,而且你覺得他疼在裡面,反而他好像一般朋友那樣用反話來安慰,這分寸感演的都很好。
陳:真實生活中真正的惺惺相惜很難。
徐:現在很難,現在的男女是以肉體的歡愉作為標準。兩個人好,你不走到那一步心裡都不踏實。就算是倆人最後成為朋友,也一定要走到那一關,再折回來。反正這是一個時代的強迫症。以前不是這樣,好多傳統中國男性給自己的定位是一個天人,天人的道德標準是什麼,佛經上說得清晰。男女兩個人相視一笑,就得到了歡愉。好多妓女行的是天人之道,檔次越高的妓女,專門有人叫跟人。你我關係好,今天留宿了,是我的跟人陪你睡覺。許多文人跟妓女行的是友道。
不光是面對男女,還有面對事業和個人成就,在人間行天道,是傳統中國男性。為什麼後來日本女的為什麼狂喜歡中國男性,就覺得中國男性魅力大,從我們的爺爺輩基本上這個觀念就崩潰,到父輩就當然無存,到我們這一輩,就不知道我們到底是什麼人。還經常說布拉德皮特多男人,其實他演的是渾小子。
陳:有場戲,葉問離開佛山去香港,妻子在後面跑著……
徐:這就是,到底是選擇詩,還是選擇生活。最早想選擇的是一個古詩,但是最終選擇的是生活。郎心自有一雙腳,隔江隔海會歸來,是一種,特別兒歌的生活裡的那種東西。這就是中國人的表達方式。中國的夫妻之道是親人之道。韓國保留這個傳統,女人稱呼老公,叫哥哥。夫妻之間反而不好表達直露的愛情,中國的傳統社會,哪有我愛你,你愛我。沒有這麼直露。越珍貴的感情,方式越婉轉。
所以葉問的夫人最後是在他手心裡寫字兒,留言。但是他留言一看,是兒歌性質的,兩個人的情誼就體現在這兒。他在夫人手上留言,其實體現的還是親人的關係。就跟爸爸在小孩兒手裡寫字一樣的。
王家衛的特點就是一旦找到了最精確的關係,他就不要其他。送別那場戲,妻子的形象就是一個手心,丈夫的形象就是一個手指。還有裡子和面子。最後宮二成了裡子,葉問成了面子。丁連山和宮老爺子他倆是裡子和面子的關係,一個成為裡子的人,一輩子都見不了眾生。他成為一個門派的隱蔽的存在。
一部電影總是有他的取捨,導演覺得能夠交出這個版本,他一定是對內在的結果滿意了。有的人對小瀋陽、張震的戲覺得有點突兀,但是這個突兀是有一定的取捨來的。其實維護的還是裡子面子,刀和刀鞘的關係。
陳:現在這兩年基努李維斯也拍《太極俠》,華誼的《太極》講的也是楊露禪,您怎麼看待這一波熱潮呢?
徐:創造一個東西的方式無非是兩種。一個是不斷地從外面找,這個我們已經用了很多年了。我們找一個洋人,打他,這個就是從外面找,或者找一些西洋的因素,不斷給舊有的武打類型充血,《太極》運用了很多連環畫的因素,動漫的朋克的手法,日式連環畫的手法在裡面,這個無可厚非。補充新鮮血液是成長過程中的必要。
但是更關鍵的是從內找,一個文化的強悍呢是向內找的一種自省能力。我們二十年來總是向外找,我們總是在格物,分析外在的物,格物致知,是知道。但你只有向內求一些東西,你才能真正得到,這才是真正的偉大的思維。反觀內心,你才能獲得生命力。心血就是這樣。
近20年來,格物的功夫已經做了很多了,學好萊塢學港片,學大眾電影,學傳播學,博采西方各種時髦的視聽符號和觀念。但是相對來說反觀內心的少。所以我覺得《一代宗師》是一部反觀內心的電影。就是你別再做什麼文化比較研究了,你拿中國的東西跟外國比,比又不是一個公平的比,你是拿蘇式美式英式,拿他們作為評判標準。反觀內心,你反觀一個民族真正的情感和骨子裡的東西來比較,看真正是什麼。
綠:你的新書《武士會》和之前的小說裡,跟女性相處,男主角都是被動的,一個螺絲,除非你是螺絲刀把他擰開。
徐:我寫的還是生活在傳統思維的人,咱們熟悉的是西式男女關係,男人的勇敢和品質,在於追求女性和表達自己。但在中國傳統裡,一個男的如果主動表白,是不尊重這個女性,是粗魯無禮。什麼時候可以?得到女性暗示時。咱們這邊西式的愛情觀太粗糙了。都是一個男人去問,然後這個女人表示猶豫不答應,然後這個男的通過各種努力,半強硬,連欺騙帶強迫改變了這個女人的想法,讓女人就範,然後哇,這個是偉大的愛情。但是你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上看,這是沒有教養的下人式的愛情。
綠:為什麼你的小說裡主角都必有一瘋?
徐:因為我寫的是特殊的人,連唱戲的都是不瘋魔不成活,更何況是習武的。在這個時代,連崔永元都得過抑鬱症了。所以我寫的是一個人間的常態,並不特殊。
作者:張愈 刊登於2月上旬《ELLE》,發表時有刪節
http://blog.sina.com.cn/u/1248569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