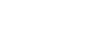胡金銓,說來有趣,我這一代的小孩是看著他電影長大的。先是他以「金銓」藝名演的《畸人艷婦》、《神仙老虎狗》、《江山美人》(飾那個唱「你要帶她走,我就跟你把命拚」的大牛)、《一樹桃花千朵紅》,我們原本就熟悉得很他那張有點胖嘟嘟卻兩眼又有點嚴厲兮兮的面孔。更別說他更早演的《金鳳》(改編自沈從文的《邊城》乎?)、與《長巷》(改編自沙千夢的同名小說)。
故而我自幼即對這個人算是不陌生。
後來的他,開始自己導演電影了,這時候的胡金銓,竟然與前面的人生稍微有點變化了。
可以說三十歲以前的胡金銓,是一個多難時代的產物。自他所演影片看來,他是個「孩子」,要不就是個幫工或跟班,顯示時代在凌亂未整前每個人能嵌在哪個位置就暫時嵌在哪個位置之處境。且看《江山美人》中的大牛,竟找了個快三十歲的他來演。再自他的人生經歷去看,似乎他隻身離開故鄉,算是避開紅禍,南渡至香港,遂不得不做上一些學徒的工作,這一段「多能鄙事」的少時,為他日後打下了「更要爭氣」的基礎。
三十歲以後的胡金銓,又幾乎是一個微顯犬儒、影片氣勢不凡、評論界常以學術角度論他、的嚴謹君子了。
這麼樣的一縷生命路數,倒是頗奇特的。同時,也可能頗辛勞。
孤身漂泊 寄情古裝電影
香港五十年代國語片會將他選角為「孩子」,一來或許編導者自手邊現成的同事朋友提取,二來或是他的長相有一股童稚氣。這種社會上認定的習慣,或許對他的成長模式,有了某些影響。也就是孩子的那一時段不易跳進青年的那一時段。後來甚至青年的時段完全模糊,直接進入中年時段。
故而後來胡金銓的電影題材,很顯然不環繞在青春愛情、男女思慕上,甚至也不著墨在家庭倫理上。哪怕家庭這一概念,在他十多歲離家前,是極深極濃的影響著他(他生活在三代同堂、四合院式的北京大家庭中)。
胡氏開始拍片時,完全不呈露當時香港的風貌,而進入自己最喜造就的歷史世界,並且其中含蘊著他出身的華北風土。即說一點,他電影中角色的語言,完全與所有國片的用語不一樣,是胡氏自己敲錘過的北方話。他對十八歲以前在家鄉北平記憶中所聽所講的尋常百姓語言,深深懷念卻又有些淡忘與隨著時日流逝後的不確定,於是在讀老舍小說時偶可重溫一點,卻又未必全面;也不時在台北的停留期間最樂意與北平出來的推行國語最力的何容(1903~1990)老先生多所相談與請益,往往將好些個字眼早年家鄉是怎麼說的,一一給勾索了出來。此一刻也,是他最快樂的學術之行,亦是溯源之旅。
猶記七十年代末,某次在台北聽他聊天,他言及香港港英政府的政策,是希望港人使用粵語,而不是國語。如此一來,香港的華人比較能掌控於英人手中。胡氏謂,他早知這種陰謀,雖會說粵語,但他儘量讓自己說國語。
胡氏的故國(或說故園)觀念,算是濃重的。他離開赤化中國,有很長(甚至終其一生)的時間極不認同共產黨,尤以五、六十年代他的大伯一家被鬥得甚悽慘,他道來很是沉痛。
這樣的他,很長一段時日,既不可能依歸中共,又未必欣賞國民黨,再加上對港英政府亦不盡滿意,稱得上一個天涯漂泊人。正好寄情於古裝電影,更好是武打片。
打鬥意趣 開創武片風格
八十年代中期,胡金銓旅居洛杉磯東郊的San Marino時,自己讀讀書、查查圖書館資料,算是逍遙自在,偶至Monterey Park華人餐館林立之地吃一盤「王家餃子館」的炒餅,便已是最慰藉他北方脾胃的上等享受了。
六十年代港產的武俠片,造型早濫,即胡氏的《大醉俠》在造型與裝具上也沒法與別的片子差異太大,只不過他的轉場與剪接比較利落罷了;然自聯邦的《龍門客棧》起,胡氏的片子便有一股「正宗」味,凜然有一襲尊貴氣。這時,人們可隱隱知道國片中的武俠片開始有講求考據的人出來矣。
胡金銓正因為有孤身一人流亡至港、參與不甚製作精良國片的配角演出等經驗,或許益發激勵他人生後來的志氣,遂在「香港時期」的奠基工程(編導《大地兒女》、《大醉俠》)後,於「台灣聯邦時期」完成了他作為「風格家」的大師地位。也就是拍了《龍門客棧》、《俠女》二片。
《龍門客棧》是1967年最賣座的國片,然它不僅叫座,亦叫好。乃《龍》片充分顯現出胡氏的場面調度。且看一場戲,蕭少鎡(石雋飾)第一次抵客棧,沒遇上吳掌櫃(曹健飾),與東廠爪牙打了一架,結果受大檔頭(苗天飾)勸停,出得門來,走至荒遼沙地,結果遠處一人拱手站立,正是吳掌櫃孤立風中,似在相待。這一場戲,饒有味道,便是胡氏的場面調度也。
《龍》片之廣受歡迎,尚有一原因,便是其類型可稱作「召集眾好漢完成一使命」片。吳掌櫃為了救于氏姊弟(忠臣于謙的遺孤),不但找了石雋,找了薛漢、上官靈鳳兄妹,後來還加入了曾遭東廠嚴罰下過蠶室、反正來歸的萬重山兄弟二人;終虧有那麼多人,最後才殺了白鷹。這種「召集好漢」片,好萊塢最有名的就是《決死突擊隊》(The Dirty Dozen),日本黑澤明的《七武士》是影史上最經典的例子。但始作俑者,當是1950年約翰.休斯頓(John Huston,1906~1987)的《夜闌人未靜》(The Asphalt Jungle)一片也。這種志士集結一堂,然後出生入死為了完成一樁大事,最能扣緊觀眾心弦。
《龍門客棧》是一部充滿打戲的片子,於是「如何安排打鬥」、「為何打」最是重要。當年胡氏妙手偶得,弄出這樣一部充滿打鬥意趣的經典武俠片,遂成就他的武打片大師之聲望。
佳作豐盛 趣味韻味兼具
三年後的《俠女》,更幽邈了,更上一層樓了;卻不知是少了股生猛氣還是什麼,當時並不賣座。然知音卻更讚賞此片,終於在1975年的坎城影展奪得委員會最高技術大獎,這對國片來說,是破天荒的殊榮。
《龍門客棧》一片的編寫模式,其實最適合胡金銓;簡單、乾脆、人物鮮明、陸續登場、最後要完成一使命。這樣的片子,最不用講太多的主題或哲理,卻是結結棍棍的純粹視覺享受。我遇過不少影迷,大夥皆這麼認為。
稍後的《三叉口》(《喜怒哀樂》中的《怒》)、《迎春閣之風波》、《忠烈圖》皆是打片,也皆不令人討厭。
尤其規模愈小、場景愈單純,愈能拍出豐富的打戲。《忠烈圖》一共沒幾堂景,有時在樹林,有時在海灘,有時在村屋,亦偶在衙門(即有屠光啟飾朱紈的部分),簡單之極,卻照樣能打出好戲。但看你想不想只拍打戲而已。
《迎春閣之風波》一片,最具魅力處,是田豐所飾的一個人物李察罕。這雖然是一打片,卻增添了一些韻味,尤以片尾韓英傑彈三絃唱關漢卿小曲,這段在刺李前的鋪排尤其動人。
《忠烈圖》中亦有一妙韻,即飾伍繼園夫人的徐楓,從頭至尾不說一語,卻叫人愈看愈覺著美、愈覺著英氣過人,真是好筆。讓她穿苗服,亦絕妙安排也。
大夥似乎不約而同有一種見解,便是胡金銓有太多可以拍出給世人看的東西,卻似乎只呈現了極少,這是最教人嘆息的。已故的遠景出版社老闆沈登恩,當年一直希望出版胡金銓各類的雜項著作,卻也倉促間只湊上了一本《山客集》。他的才能太多,畫他畫得好,明史他讀得好,老舍的文章他研究得好,太多太多,這造成拍電影亦可能分神嗎?不知道。
他應該專注於把劇本編寫得更完善,或覓得更適宜的合寫者,或找到更好的製片替他先張羅寫故事之人……等等之或許。然而誰是這樣的合編者?誰是這樣夠意思又體恤他的製片?
人生如戲 一代大導留名
胡導演其實一路走來遇著的貴人並不少,像早期的夏維堂、沙榮峰,或後期的胡樹儒,皆在他的拍片生涯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再就是,有太多敬重他、視他為恩師的終生好友,像鄭佩佩、石雋、徐楓、張艾嘉等,總是人前人後為胡導演解釋外人不夠理解的片中瑣節、為胡導演找尋更優厚的拍片機會、為胡導演張羅新片可能徵召的人才與錢財。這些年輕時跟著他演戲的人,本身已然蘊涵了俠士俠女的義風,這是國片中最了不起的道德倫理。
他應該可以找到相當說得過去的資金(即使不必太多),他也應該可以找到相當有陣容的大牌為他擔綱演出,甚至他還可以隨你想怎麼拍就怎麼拍、事後別人再來埋單,皆可能也。其實哪有這麼困難呢?只要你胡導演自己審時度勢、找到最可發揮的時機與最稱意的合作夥伴,便何事不能成?
當然,人生如戲,拍出怎樣的好電影與怎樣籌拍電影,有時後者更難。誰能人生像電影每場戲皆調度得既高低有致又圓融沉厚、渾然天成呢?
●「胡說八道──胡金銓武藝新傳」特展,7月3日至8月26日於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市長安西路39號)舉行,全面展現胡金銓電影、漫畫、手稿、分鏡表、場景圖、人物服裝造型圖、書法、繪畫……等作品。詳情洽電:02-25593874。
作者:舒國治 中國時報 2012-07-02
http://news.chinatimes.com/reading/11051301/112012070200037.html